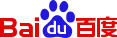由此,在将法理作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中,法理学的范畴体系则是值得重新认真思考和系统阐述的论题。
比如,在儒家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即正义。法理学的这种研究范式必将会使部门法学更加注重对自身领域问题的深入性思考和研究,更加注重说理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促使法理研究范式在部门法学中更广泛地运用,同时也会激发部门法学者对自身研究范式等本学科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意识和研究动力。

然而,是否真的就如论者们所言,法理学,更确切地讲是中国法理学就没有存在过,或者已经死亡了呢?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式的理性反思,任何本质主义的论断都是封闭式的,意味着语言专制和暴力的危险。在本文结束之际,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旨在建构什么,更未必能够带来知识上的增量,因为不论是对法理学死亡论争本身,尤其是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的理解和把握是否精准到位,还是对法理与法理学、法理学与法学相关理论的阐释的合理性如何,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长期论辩的论题。目前,传统部门法学如民商法学、刑法学虽获得了稳定的部门法地位,但是对于其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关注并不是太多,远未能成为该学科共同关注的论题。本文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法理时代 中国法学 。这意味着每个人在体力知识、智力、信息知晓度等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
[39] 前注17,[德]考夫曼书,第9、11页。[23]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法理学的问题,整个中国法学界都存在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问题[24]。由此,在本文看来,正是法理学这种价值多元的所谓主观性特征,才使法理学与其它以关注规范法学为根基的部门法学区别开来,使其具有更一般性、普遍性,解决整个法学以及法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关系的根本性、核心性问题,从而才使其具有的独立性存在的学科与学术意义。
由此,有人提出了人权的终结[37]。在库恩那里,范式代表科学界的世界观,指导和决定问题、数据和理论的选择,直到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使初学者从一个不知法治、权利、正义、自由等为何物,甚至满脑子是人治、权力、服从等前现代行为意识和习惯的非法律人初步成为一个市民和公民意识的现代人。后现代哲学对以往这种类似于上帝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立场进行了颠覆式批判,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乃至人类的所有领域的知识论角度,哈耶克所言的人之理性所不及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认为,至少应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法理应当法理学的逻辑起点,并贯穿于其整个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副标题就是论正义,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把正义理论发展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并对城邦正义等进行了详尽阐述。

[61]美国哲人约翰·罗尔斯在论述了其国内政治自由主义理想的基础上,也像康德一样,提出了建立世界政治自由主义理想秩序的方案,即万民法,意指规制人民相互间政治关系的特殊政治原则,一种自由人民的联盟。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例,其主要起草人未加拿大法学专家约翰·汉弗莱和其他参与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黎巴嫩的夏尔·马利克、新加坡籍华人吴德耀、中国的张彭春和法国的勒内·卡森等人,其中思想家占多数。[18] 陈辉:《德国法教义学的结构与演变》(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我们秉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并非是言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封闭僵化的教条主义,我们更应秉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比如,社会学关注的社会问题,怎么不可能是法学要关注的问题。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的基石与材料,也是研究范式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中正义的具体体现截然相反,否则就违背了正义的精神和原则。但是,此标准并非判断所有学科的唯一且正确的判准。
比如,在儒家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即正义。法理学的这种研究范式必将会使部门法学更加注重对自身领域问题的深入性思考和研究,更加注重说理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促使法理研究范式在部门法学中更广泛地运用,同时也会激发部门法学者对自身研究范式等本学科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意识和研究动力。

然而,是否真的就如论者们所言,法理学,更确切地讲是中国法理学就没有存在过,或者已经死亡了呢?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式的理性反思,任何本质主义的论断都是封闭式的,意味着语言专制和暴力的危险。在本文结束之际,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旨在建构什么,更未必能够带来知识上的增量,因为不论是对法理学死亡论争本身,尤其是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的理解和把握是否精准到位,还是对法理与法理学、法理学与法学相关理论的阐释的合理性如何,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长期论辩的论题。
目前,传统部门法学如民商法学、刑法学虽获得了稳定的部门法地位,但是对于其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关注并不是太多,远未能成为该学科共同关注的论题。本文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法理时代 中国法学 。这意味着每个人在体力知识、智力、信息知晓度等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39] 前注17,[德]考夫曼书,第9、11页。[23]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法理学的问题,整个中国法学界都存在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问题[24]。可以说,法与法学天生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社会以来的几个世纪,我们在世界上逐渐被西方追赶并超越,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也日益走向封闭和僵化,从而导致创新意识和能力严重不足。而对于一个部门法学学科而言,仅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仅仅是在作为部门法获得独立地位的标准,仅有研究对象也不足以获得该学科在学理上的对立地位。
[55] 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由此,针对这种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不同的法律部门进行校正。
因存在政治法理学者与明星法理学者,使中国法理学有颗不安分的心。以上方面往往是在对方有了法理上的行动后,我们才想起被动性运用法理来回应。
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中国法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责任不仅是物质的帮助和给予,还包括对生态、疾病等人类共同难题的应对,更包括价值理念的、精神层面的引领。但是,这种学科的划分也带来人们认识问题和思维的狭隘化。因为,任何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然是对现实具体问题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的产物,旨在为分析和解决现实具体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10]如果不面对这一实际国情,则这样的法理学教材更是不切实际,缺乏问题导向的。在晚近兴起的社会法中,正义的集中表现既不是自由,也不是秩序,更不是效率,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即给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群体的人的倾斜性保障,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与此类似,法理也应成为法理学、乃至法学的思维方式,在我们面临纷繁复杂的各类理论及现实问题时提供发现问题、解释问题、推进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意识、路径和方法。论者以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为例,试图证成只有多位学者遵循某一最大公约数才可能称之为某一流派。
如前所述,法理学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如论者所论述的类似于部门法的规范法学或法律史学的历史材料?如果法理学的根基本就不该是如此之类的东西,那如何又能论断失去了根基呢?至于信仰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作为一个学科与部门法所称的研究对象不完全一致。
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欧美,还是日本,乃至前苏联,对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而言,都是舶来品。中国目前的诸多问题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的权益保障就能解决的。也只有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和贯穿始终的方法论的法理学,才能担当引领整个法学的重任。[31]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2页。
[29] 陈金钊:《法理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既有基本理论研究,又有新兴领域研究。
第三,正义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具有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与宗教、伦理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很好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是社会正义或社会问题能否进入法学研究领域的联结点。即便是论者当下我国法理学教材所总结出真实现状,这也不能就为中国法理学面临死亡提供证成性依据。
范式(paradigm)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他试图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结合起来,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界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内史与外史结合起来,以对科学发展规律进行综合考察。当今世界不同于殖民时期以及以前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凡事要讲法和法理,而不能仅靠过去那种帝国主义的力量显示的方式,尽管国家的强大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坚强后盾和关键力量。